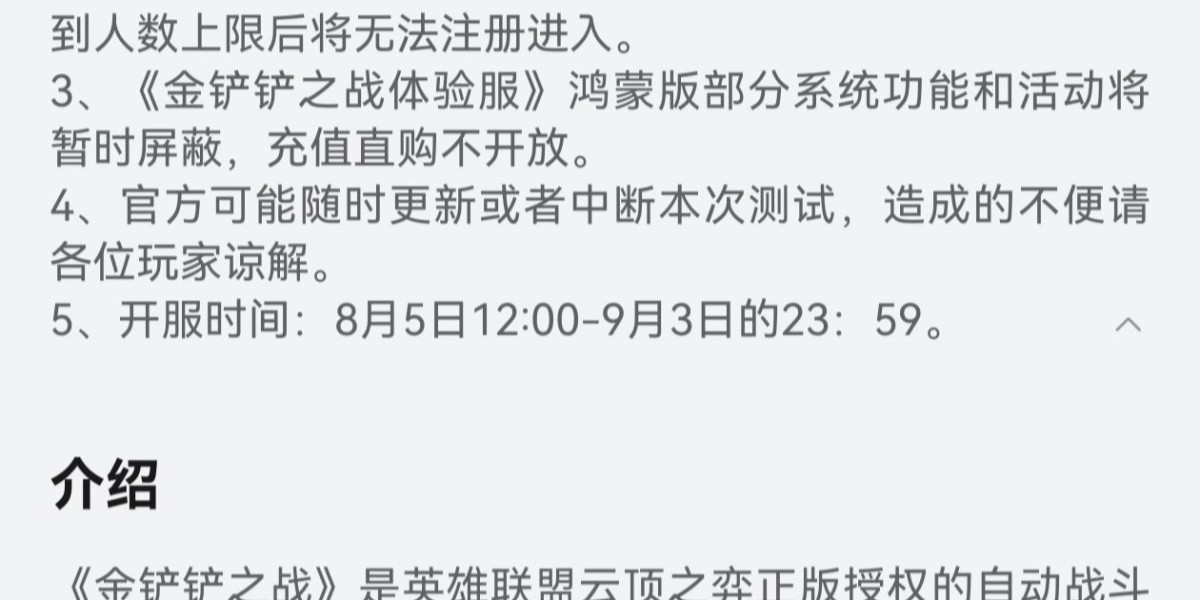本文转自:潮州日报
辗转艺途多历练 守望艺苑永流芳
——潮州戏剧艺人访谈摘录之沈雪华篇
▲上世纪五十年代《纱窗会》剧照 (沈雪华饰演赵五娘,王良华饰演蔡伯喈)
□ 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 陈东 许镇焕
沈雪华,女,1938年生,广东潮州市人。读小学时开始参加潮州市第二街道办事处四大组业余宣传队演出,后宣传队转为正天香潮剧团而成为职业演员,在《纱窗会》《琵琶记》等多个剧目担任主要角色,参与《八仙闹海》《齐王求将》《三关排宴》三出剧目的录音,1978年在潮安文艺培训班任教,培养了不少潮剧后备人才。
正天香潮剧团
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年,1950年末,办事处号召各个大组(办事处属下的组织机构)组织宣传工作,其实就是上面有什么政策或紧急任务需要宣传,编剧先生就编写一个小节目,组织“厝边头尾”一些十一二岁的小孩在空闲时间集中起来演唱,那会儿节目很多。当时那个组叫第二街道办事处四大组业余宣传队。编剧先生俗名叫柯老三,本名叫柯静呆,他人特别好,把我们这些小孩都看作自己小孩一样。还有一位作曲老师,我已经记不起来叫什么了,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后来没有来剧团,只有在业余阶段。宣传队就是这两位老师为起点,一人写词一人作曲,离不开他们。宣传队男演员有蔡崇孝、王良华(又名王天赐)和黄汉章,赐兄晚些加入的;女演员我记得有良珠、桃姐、秀芬、黄妙娥,几个人一组。乐队人也不多,打鼓的是丁千林先生,乐队头手是周才先生。后来一位作曲先生我记得是林寿光。大组长是丁勤,还有积极参加组织活动的林传耀,也是后来的团长,这两位就是宣传队的核心。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这些,还有办事处两位主任也很热心,一位姓柯,一位叫业景,常常来关心我们,没有他们的重视也办不起来。
办事处就在现在的红厝埕。有一个大门楼,得走台阶下去,当时是地主厝,家里只剩下老大家(婆婆)、儿媳妇和女儿三人,她们住在前厅。那里很大,大门楼往下走到大埕,一半种着树,一半可以过去火巷,天井、后厅就在这,林团长当时就住后厅。这里就成了当时的活动场地,可以排练。
小孩们会在晚饭后集中,先学习编剧写的内容,词、唱段什么的,学好了就出发去演出。演出地点就在现在牌坊街要转入东门的这个路口,这里晚上最热闹,人最多,适合宣传,路人可以停下来听,也不会妨碍交通。我们就在马路牙子上,当时是一家食店,打鼓师傅和乐队坐后面,我们就在前面唱,路人听到了就凑过来看。有时候很热闹,得有六七十人在那听。
宣传组这段时间挺长的,得有三四年,从1951年起,一直到1954年还是1955年才转为半职业,1956年6月再转为职业剧团,也就是正天香潮剧团。期间我们都是积极热情地投入,甚至有时候还自己补贴一些东西。
“单线”舞台
我当时在城南小学读书,白天读书,晚上吃完饭就来参加宣传活动。组里的人相处得很融洽,就这么一直坚持着到能演大戏。当时编排了很多大戏,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纱窗会》《琵琶记》,都是生旦戏,还都是全剧的。《纱窗会》一开始只演了扫窗那一场,后来可能柯老师给编成了全剧,演了一整晚,有头有尾的。《琵琶记》也是,就是《蔡伯喈别五娘》,剧情大同小异。其实一开始,宣传时期也好,业余时期也好,我演的就是“假男性”,做女小生,《纱窗会》我演的高文举,《琵琶记》我演的蔡伯喈。后来潮剧行业转大小生(即男小生),赐兄就演高文举和蔡伯喈,我则转来演王金真和赵五娘,这差不多是我转为职业演员的时候。演男角也演了至少三年,演了挺多戏的。我留着一张当时《纱窗会》的照片,和赐兄的合照,那时我才十六七岁,赐兄比我大七岁。
1959年之前还是“单线”角色,一天演三场,早上化好妆,八点多开始演出,一直到十一点多休息吃饭,一点多开始另一场演出,就这样这个妆从早上维持到晚上十二点多,“单线的”,没有人替换。有时候真的很辛苦,毕竟还是小孩子,但是大家都一样,而且氛围很好、很和谐,再累也坚持着完成任务。1959年末,余丽珊等人从汕头戏校毕业入团后,我不用再“单线”演出,有了去汕头戏曲学校进修一年的机会。这一年,老师在“唱念做打”各方面的正式教学指导,让我提高了不少水平。
1965年稻香和正天香潮剧团合团,很多人被 淘汰了,我也在1968年被下放了。1972年初,商业宣传队成立,需要吸收一些剧团的人,就来找我了,谈了很多次,我就应承了。那会儿演的戏有《迎风山》这些现代戏,到处去演出,就这样我在商业宣传队演了两年时间,因为身体原因才停止演出。
1978年,文化局的吴士衡局长和林继杰副局长他们来做工作,让我去戏校,便调了过去。那会儿是戏校第二期,有李玉兰等,第一期也有几个学生在校,像杨莉、潘亚顺和萧小玲。第二期学生毕业时演了《杨八姐闯幽州》。这一次演了整出戏,而且一出去就演了几个月。这一期的演出之后,戏校就分成了梨园学馆和潮安文艺培训班,分后没多久又合并了,合并之后我就调走了。
下乡演出记忆
想想还挺好玩的,那会儿我下午读书,晚上得到文祠、归湖、登塘等地演出,放学后就沿着田埂走,走到太阳落山了,刚好到那化妆,之后演出到凌晨一点。当时不只有一出大戏,三小时大戏前还有近一小时的短戏演出,所以起码要演出四小时,时间短了观众们还不乐意。那时候三更半夜特别冷,观众席放着“摔斗”(打谷桶),那些阿姨阿伯就坐在“摔斗”里面探着头看戏。我们演出结束后就立马收拾头饰、卸妆,然后再走回来,走到天色渐亮,一边走一边打瞌睡。真的很辛苦,脸盆什么的都得自己背着,除了被褥可以跟着道具让车载走,其他的日常用品都是自己背着。到乡下演出住老祠堂,睡的也是草垫,在大戏园演出偶尔才有床铺,我们都是在草垫上铺被褥,拿布帘隔开,里面一排女的住,中间一排住着领导,另一排给男的住,六七十人就这么挤一起住,领导那一排为了办公,多了灯光和桌子。但那时候大家都很投入,虽然很疲劳,但觉得新奇、有趣,自愿地来宣传,没有半点私心,领导说什么时间在哪演出,就都积极主动地参加,没有怨言。这一代人很能吃苦,也单纯,心无杂念,无论是谁,都做到对得起自己。现在环境条件、待遇什么好了,简直天和地的差别,所以更要知足、珍惜。
(本文根据沈雪华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