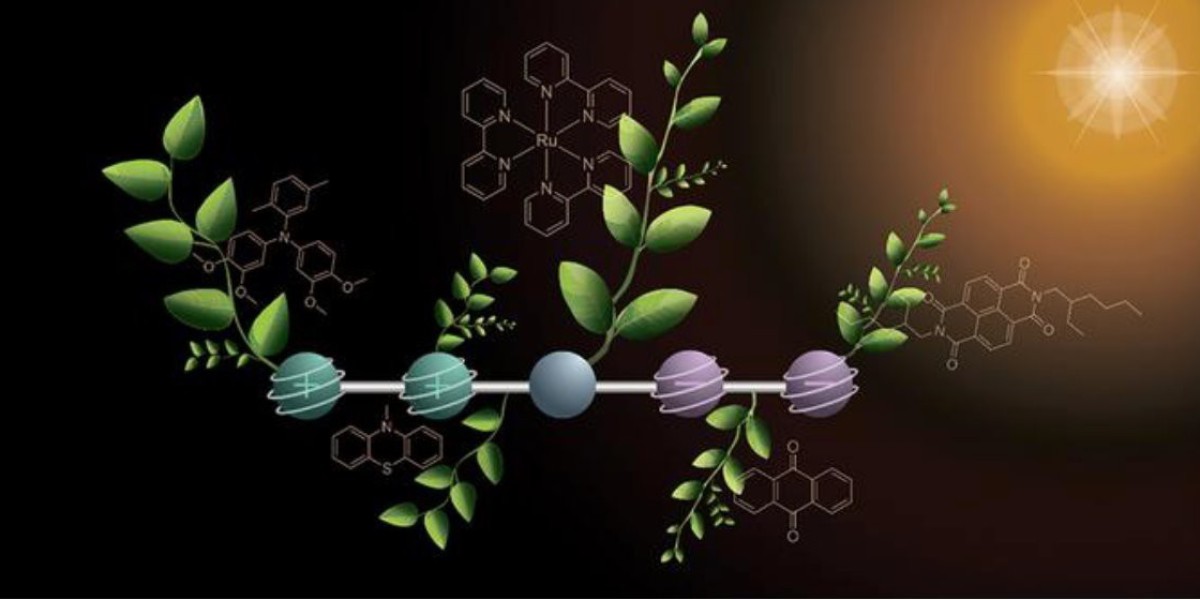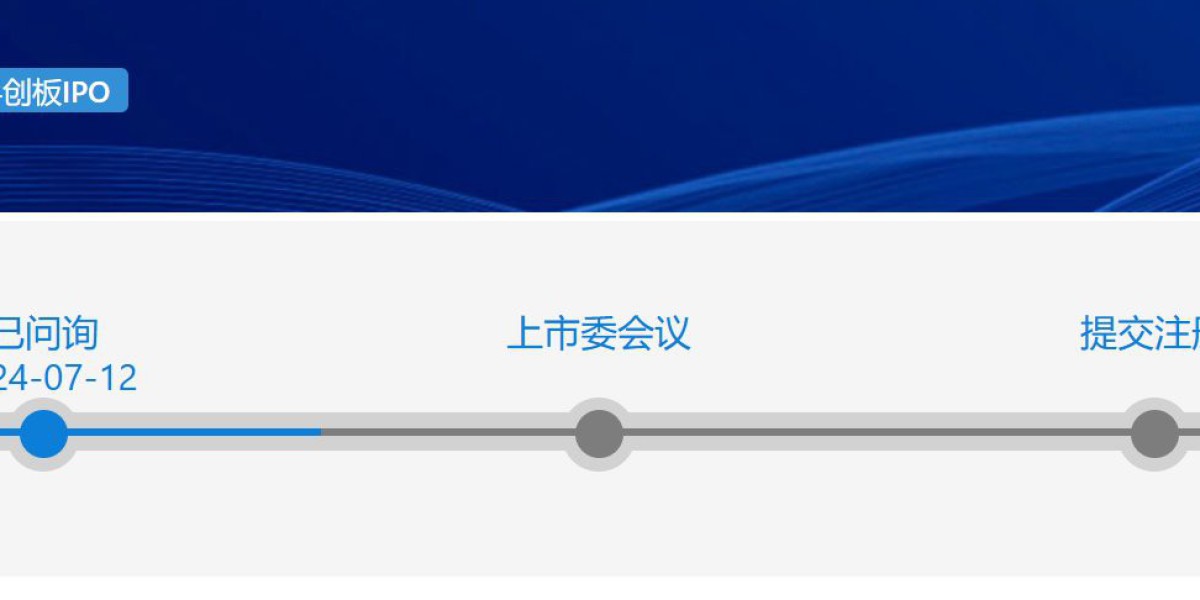去年暑期,俄裔美国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Alexei Kitaev在北京出席2024国际基础科学大会(ICBS)时,获颁基础科学终身成就奖。
Kitaev在理论物理和量子计算领域具有深远影响,他是量子信息理论的先驱人物,他开创性的工作奠定了现代量子比特设备中量子纠错方案的基础。他还引入了极具影响力的二维量子自旋液体的可解模型,以及有全息描述的量子引力可解模型。
Kitaev一直在物理领域工作,却同样对数学领域充满热情。他回忆了在大学本科时偶然发现的俄罗斯数学家Yuri Manin的著作《可计算与不可计算》,这是一本关于数学逻辑的书,提到了量子力学的复杂性可能带来的新的计算方式。正是这本书激发了Kitaev对量子计算的兴趣,促使他开始了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他还强调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并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分享了他是如何从量子计算领域转向其他研究课题。
ICBS会议期间,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顾颖飞研究员对Kitaev进行了专访。本文是访谈视频的中文翻译版,由ICBS独家授权《返朴》整理、翻译。
访谈现场,左为Kitaev | 视频、图片由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独家授权
受访 | Alexei Kitaev
采访 | 顾颖飞
翻译 | 叶凌远
视频 | 王若水、牛芸、王一婷、余景浩
顾颖飞: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的顾颖飞。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Alexei Kitaev。Alexei,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邀请。很高兴在中国见到您,也祝贺您获奖。
Kitaev:谢谢。
顾:有些朋友可能对您和您的工作不是特别熟悉,能否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Kitaev:我是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主要从事理论物理中各种问题的研究。我第一项成功的工作是和当时的同学Leonid Levitov、Pavel Kalugin一起完成的,那时我们都是朗道研究所的学生。那项研究是关于准晶体的。后来,我开始研究量子计算,包括量子算法和量子纠错码。我对“如何保护量子信息”这一问题感兴趣,因此转向了拓扑量子相(topological quantum phase)的研究。
拓扑量子相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状态,通常在极低温度下出现于某些相互作用的电子或自旋体系中。这类物态有一个很好的特性,就是它们可以存储并保护量子信息免受错误干扰——后者正是我进入这一领域的初衷,这源于我在量子计算领域的工作,随后我专注于拓扑量子相本身。
在此过程中,我提出了多个模型,例如环面码(toric code)、表面码(surface code),还有马约拉纳链(Majorana chain)、蜂窝模型(honeycomb model)等。后来,我对量子混沌及其与黑洞的联系产生了兴趣,这一问题催生了所谓的Sachdev-Ye-Kitaev(SYK)模型。Subir Sachdev和叶锦武此前构造了一个模型,尽管较为复杂,但它的特性能反映黑洞和量子混沌之间的联系。我预料它应该成立,但没办法确信这一点。于是我对这个模型进行了简化,使它更容易求解。
以上就是我迄今涉足的几个主要方向。现在,我的兴趣又回到了拓扑量子相,但这次我更多关注它们的数学结构。目前,我正专注于一个听起来可能有些无聊的问题——也许确实无聊,但为了取得进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在数学上定义一个拓扑量子态。我希望这能帮助澄清一些人们试图忽略的微妙之处,或许这些细节确实只是“技术性”的。可能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
物理模型应“抓大放小”
顾:您在构建“玩具模型”来抓住物理系统本质方面的能力非常出众,可以说无与伦比。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Kitaev:在我职业生涯非常早期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喜欢这样的模型。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的工作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提出了一个关于自旋杂质(spin impurity)的模型。当时我还是一名学习应用数学的本科生,但在偶然读到安德森的这篇论文后,我被深深吸引,意识到凝聚态物理是一个令人振奋的领域。
顾:那是篇有关近藤效应模型的论文吗?
Kitaev:不是,文章探讨的是一个更基础的杂质问题:杂质是否会携带一个局域化的自旋,或者这个自旋是否会被“淬灭”。模型涉及局域态和自由态之间的耦合以及相互作用。
顾:我明白了。您的一大专长是让模型具有可解性。您在构建模型之初就考虑这一点吗,还是只考虑设计有趣的模型?
Kitaev:一开始,我只是尝试设计一些有趣的模型,它们基本上一次只抓住一个要素。我努力去除不必要的复杂性,构建的模型拥有若干有趣性质,但不拘泥于细枝末节。正是这种简化,让这些模型更容易研究。
顾:您的许多模型总是会有一套完善的理论与之相辅相成。您是在构造模型之前就对这样的理论有所设想,还是在仔细研究自己模型的过程中,才真正意识到或发现了背后的理论?
Kitaev:在构造一个模型时,你通常会对它所描述的现象有一些想法,因此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当你写下这个模型并尝试求解它时,就会发现新的东西,这基本上也是构造模型的初衷。
顾:让我们就此展开谈谈。比如以环面码为例,您的设计初衷是什么?之后又有什么新发现?
Kitaev:环面码是一种量子纠错码,旨在保护量子信息——我想设计一种能够容忍大量错误且可扩展的量子纠错码。当时我知道分数量子霍尔效应。我读到过一些论文,其中指出在环面上分数量子霍尔体系的基态是简并的。
顾:那是在什么时候?
Kitaev:基态的简并性是在1980年代发现的。我记不清具体的时间。但我在读研究生时就已对量子霍尔效应有所了解,或许不知道这一具体的结论,但对整个方向是了解的。我意识到这种简并性与量子纠错码有相似之处。而我工作的关键在于,确切地说明它的确是一种量子纠错码,在一定程度上能抵抗扰动。当然,另一个方面是简化模型。环面码本身相当简洁。
顾:从您第一次读到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到后来构造这样一种量子纠错码,中间隔了好几年。但您早期的学习经历会有所帮助和启发。
Kitaev:是的。
预料之外的发现
顾:在您建立环面码模型并加以研究之后,有哪些新的发现?最大的惊喜是什么?
Kitaev:惊喜?我不确定有没有特别大的惊喜。但在写下该模型之后,我研究了它在扰动下的表现。其中一项研究的主要结果其实并不新颖。它和Eduardo Fradkin、Stephen H. Shenker之前研究的是同一个模型,只是表述方式不同。事实上,他们的工作是许多年之前就有的了。只是他们将该模型考虑成了量子场论或者说统计物理的模型,而不是用量子哈密顿量来描述。我认识到这两种表述之间有联系。和其他合作者一起,我们也对该模型的稳定性进行了数值模拟。除了预期内的现象,我们也发现了该模型一些意料之外的行为。这些行为和我最初关心的量子纠错码的性质并不相关。这是和Philip Stamp、Igor Tupitsyn以及Nikolay Prokof'ev的工作。
顾:我明白了。我们来谈谈您的蜂窝模型吧。那篇论文有一个很长的附录。现在看来,附录中的每个小节都非常重要,一些甚至发展成了独立的子研究领域。您是如何将这么多想法,或者说数学结构与单一模型联系起来的?您脑海中有哪些要素将所有这些整合到一个模型中?
Kitaev:蜂窝模型包含任意子(anyons),其中一个附录正是关于任意子的。我并不是任意子理论的发明者,这一理论是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共同推进的成果,例如Edward Witten,他发现了陈-西蒙斯理论和琼斯多项式之间的联系。
我则采用了一个基于模张量范畴(modular tensor category)、融合规则(fusion rule)和辫结构(braiding)的数学表述,并仔细地写下了其物理特性的表述方式,以便凝聚态物理学家理解。实际上我据此研究了蜂窝模型。我不知道该模型会有这种类型的任意子。为此我得去解一些方程。这篇附录包含了这些方程。
其他附录则略有不同,或许它们包含更多原创性的工作,特别是用关联函数来表述手性中心电荷(chiral central charge),这是我的想法。
顾:那SYK模型呢?跟我们讲讲您是如何发明这个模型的。最初的目的是什么?您发现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
Kitaev:最初的动机是想理解黑洞视界附近会发生什么。
顾:在此之前,据我所知您主要做的是凝聚态物理和量子信息,是什么吸引您开始关注引力问题的?
Kitaev:这个问题本身非常吸引人,我想这是最主要的动机。同时,当时有很多关于全息原理(holography)及其与凝聚态现象联系的讨论,我对此有些怀疑,想弄清楚全息原理到底意味着什么。
顾:于是您想设计一个具体明确的模型。
Kitaev:对。而且令人欣喜的是,SYK模型确实包含了某些全息特性,但并不是完全全息的,这和在超对称模型中发现的全息性有一定区别。
顾:您构造了这个模型,它确实帮您澄清了许多问题。在研究SYK模型时,最让您意外的是什么?
Kitaev:让我从我预料之内的发现谈起。我预测非时序关联函数(out-of-time correlator)会随着黑洞大小指数增长。这被称为极大混沌(maximal chaos)。幸运的是,在该模型下这的确是正确的。但我没有预料到其技术细节。其中一点是微分同胚的不变性:该模型的Schwinger-Dyson方程对微分同胚变换保持不变。这使得在一个圆上,应取低温极限。与之相关的是Schwarzian作用。这两点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它们只有在深入研究模型时才会被发现。
苏联教育体系何以英才辈出?
顾:我意识到您许多工作都和数学紧密相关。俄罗斯(苏联)历史上涌现了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您觉得苏联的教育体系是否有一些独特之处,能够培养出这么多人才?
Kitaev:我认为有一个方面很重要,那就是高中教育。在高中教育阶段曾有一种制度——我希望至今它仍有一部分保留着,就是所谓的数学学校。莫斯科有一些非常精英的学校,或许其他城市也有。许多有天分的学生会在高中最后两年来到这类学校学习,接受更加深入的数学训练。就我成长的城市沃罗涅日(Voronezh)而言,虽然当时人口不到百万,但仍有两所这样的学校。来自各个学校的学生,包括周围小城镇的学生,会到这两所学校学习更深入的数学课程。
顾:上这样的学校需要申请吗?
Kitaev:是的,会有面试,他们会挑选有能力的学生。
顾:这些课程是专攻数学吗?还是也有物理和其他课程?
Kitaev:主要是数学课程比普通中学更深入,也会多学一些物理,但核心还是数学。
顾:但您进入大学之后,在某个阶段选择了将更多时间用于研究物理。物理学中是什么吸引了您?
Kitaev:我一直对数学和物理都感兴趣。有几个因素影响了我的选择:我在中学时参加过苏联的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并获得过奖项;而我没有尝试参加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我虽然也尝试过求解国际数学奥赛题,但大概只能解出三分之一的题目。我感觉自己在物理方面的优势更明显。
顾:因此那时您决定在进入大学后学习物理?
Kitaev:是的。或许可以一提的是,我的大学——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有一个特别项目。我们有两个理论组,会组织一个额外的入学考试。通过那次考试,我从应用数学转到了物理学,具体来说是理论物理学。实际上,通过考试有两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学完规定要求的朗道理论物理课程,但我做不到。我是通过考试转到了物理学。
顾:您曾在朗道研究所工作了几年,随后又搬到了美国。在您看来,俄罗斯(苏联)早年的科研环境和后来到美国之后的科研环境有哪些差异?
Kitaev:我是在1984年前后进入朗道研究所的,那时我还是一名学生。那段经历非常精彩。研究所里有许多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涉及各个领域。如果你有任何理论物理的问题,总能找到合适的人请教,这非常令人兴奋。
但后来,苏联解体,整个体系崩塌,经济状况恶化,大多数科学家都离开了俄罗斯。我又在国内坚持了几年,通过去国外短期访问,比如魏茨曼科学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来补贴收入。那段时间俄罗斯的经济非常困难,科学家的处境也堪忧。好在我通过一些短期的职位获得了一些收入。我不想离开,也曾希望状况会变好,但事实上没有。最后我意识到,如果我想继续学术生涯,去其他国家是更好的选择。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顾:谢谢您的分享。这部分谈到了您在物理上的独特风格以及您的经历。现在我想把话题转向您研究中的跨学科方面。您在凝聚态物理和量子信息两个领域都有重要贡献,这两个领域也确实因为交叉融合而获益匪浅。我想请问您个人的经验:这种交叉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您的凝聚态物理背景如何影响您早期在量子信息和量子计算方面的工作?反过来,早期在量子信息领域的工作,又如何影响您后来在凝聚态物理和引力方面的研究?
Kitaev:我提到过环面码和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例子:我在凝聚态物理中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应用到量子信息中去。反过来也是一样。比如,我意识到某些物理系统具有容错性,能抵抗扰动。我提到过任意子,特别是非阿贝尔任意子。非阿贝尔任意子会导致简并态的出现。当拥有两个或更多的任意子时,这种简并性与它们的融合通道(fusion channel)有关。在我研究任意子之前,这一点其实已经有人知道了,但当时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量子纠错码,使得这样的系统具有量子容错性。
顾:我明白了。所以说,某方面的经验会带来更广阔的视野,也可能激发新的解决思路。
Kitaev:正是如此。
顾:您当时开始研究量子信息的时候,其实这个领域刚刚起步。最初是什么吸引您进入了这个领域?有没有哪项具体的工作鼓舞您投身这个方向?
Kitaev:我会说,当时这个方向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研究领域,但那时正是一个契机。我第一次接触到量子计算的想法是在本科时期,我读了Yuri Manin写的一本书,叫《可计算与不可计算》(Computable and Uncomputable)。这是一本关于数理逻辑的书,在导言里他提到了几个逻辑与现实世界可能相关联的场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量子力学。他用两段话表达了一个思想:量子力学有复杂的计算结构,这也许会带来一种新的计算模型。这让我非常兴奋。我知道有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问题存在,但在我进一步了解新的进展之前,还没法深入思考。后来我阅读了费曼关于量子计算的几篇文章,一篇是1982年的,另一篇可能是1985年的。我可能记错了具体年份。
顾:我记得费曼是1981年做的报告,论文是第二年发表的。
Kitaev:也许是1981年。(编注:经查证,费曼于1981年在MIT举办的第一届“计算与物理”大会上给出了一个关于模拟量子计算的报告。)但即便读了这些文章,我当时还不足以开始动手研究。后来我了解到了量子计算的数学模型,那才是我真正的研究起点。有了问题的精确定义,才可能取得进展。在那之前,这个问题的表述一直太模糊。
顾:您是在研究生期间还是在毕业之后开始这项研究的?
Kitaev:是在毕业之后。
顾:对于一些更具体的工作,像您定义了QMA复杂类,或者后来您发现的量子相位估计算法,这些发现是由领域内的一些发展推动的,还是您在独立研究时自然而然想到要做的?
Kitaev:相位估计算法是我为了解决离散对数问题而提出的方法。我听说了Peter Shor的结果,他解决了离散对数问题。在我拿到Shor的论文之前,我自己也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解决方法就是相位估计算法。而QMA是基于费曼的“时钟”思想,我只是对这个想法进行了形式化。
顾:现在30年过去了,量子信息这个领域发展迅速,尤其是在实验方面。如果您年轻30岁,正准备在这个领域开始研究,您会选择什么方向?我很好奇。
Kitaev:量子信息吗?我可能不会选择量子信息。让我解释一下。上世纪90年代中期,量子信息是个黄金时期,它是基础物理的一部分。但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应用性领域了。当然还是有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说,最近几年在量子纠错码方面有突破,特别是所谓的LDPC码(低密度奇偶校验码)。将来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突破,也可能会出现全新的量子算法,谁知道呢。但要找到一个新的量子算法,我认为必须既懂量子力学,又懂量子计算,同时还要懂一些高级的数学理论,比如代数几何或数论之类的,才能把这些知识连接起来。
顾:我明白了。您与一些不同背景的人合作过,比如数学家Michael Freedman,物理学家John Preskill,以及一些博士后。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合作风格?这些合作者对您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Kitaev:物理和数学方面的合作有很多种形式:有时候是一起写论文,有时候只是讨论各种问题。我特别喜欢那种思想互补的合作,我和合作者的想法能够相互补充,这种碰撞非常有趣。
顾:是的。
Kitaev:而只是讨论物理问题又有不同的体验。在与Preskill的讨论中,我学到了许多场论和量子信息的思想;与Freedman合作时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深刻的数学概念,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讲解者。
顾:所以他是一位优秀的老师?
Kitaev:我想是的。
现在的中国学生更敢说“不”
顾:太好了。现在我想谈谈您首次来中国的体验。我们知道这是您第一次来中国,您目前感觉如何?
Kitaev:首先,我非常感谢您和其他同事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我知道整个过程非常劳心费力,我真的很感激大家的好客之情。
顾:这是我的荣幸。亲眼看到中国后,与您之前的想象相比,有什么相同或不同之处吗?有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您的地方?
Kitaev:我还在慢慢体会。我觉得这里的人们普遍很开心,这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整个社会运转得很好,我也在努力理解它是如何运转的。
顾: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您这几十年来肯定和许多中国学者有过交流。与二三十年前相比,您认为当今中国的学生和年轻学者有哪些不同?
Kitaev:现在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博士后有更好的物理基础,英语也更好。二十年前我常常感到沮丧,因为很多中国学生不太敢在讨论中表达观点。而讨论物理问题时,有时需要直言不讳,比如意识到对方可能错了时需要明确地说“不”。当我向一个人提出问题时,我是真的期待一个“是”或“不是”的答案,这个答案很重要。以前他们害怕交流,而现在的年轻人则能更自如地面对这样的场景。
顾:我明白了,可以说他们更放松了。最后,您能不能对那些正在读您的论文、学习您的工作的年轻科学家和学者说几句话?无论是建议、勉励,或是忠告。
Kitaev:我认为没有所谓“万能的建议”,因为每个人的优势和兴趣不同。重要的是去尝试各种可能性,找到自己擅长和感兴趣的方向,然后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
顾: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也祝您在中国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Kitaev:谢谢!
特 别 提 示
1. 进入『返朴』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精品专栏“,可查阅不同主题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朴』提供按月检索文章功能。关注公众号,回复四位数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获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类推。
版权说明:欢迎个人转发,任何形式的媒体或机构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和摘编。转载授权请在「返朴」微信公众号内联系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