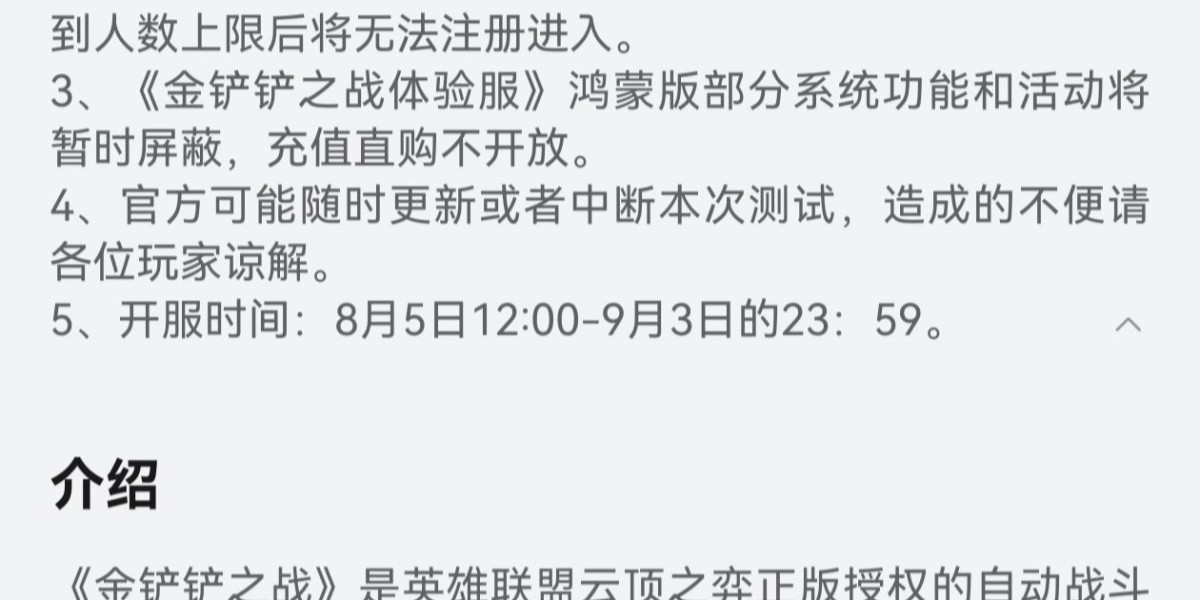“U doet wat, precies, meneer?” 我这位时髦的二十几岁发型师投来困惑的目光“您到底在干什么,先生?” 我并没有表现得像个英国人。我刚告诉她,我已经买了阿姆斯特丹宏伟的Ziggo Dome里“年度音乐节”(Muziekfeest van het Jaar)的门票这是一场为期两夜的盛会,现场将被录制并在除夕夜播出,堪称荷兰版的Jools Holland《Hootenanny》,全程献给那种充满铜管、感伤、常常难以却仍极受欢迎的荷兰流行音乐——levenslied。
“Levenslied”大致为“关于生活的歌”。它在全国各地都很流行,尤其在北布拉班特省,但人们通常把它与阿姆斯特丹,特别是昔日工人阶层聚居的约尔丹区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社交和本土音乐,levenslied关注家庭、朋友和亲密伙伴。其风格上与20世纪法国的埃迪特·皮亚弗(Edith Piaf)现实主义香颂(chanson réaliste)相通,在欢快时刻又与德国的schlager产生共鸣。
但levenslied比它的“表亲”更为感伤、宽容,拥有独特的荷兰温情——那种与家庭、家园相连的舒适氛围(gezelligheid)。它还有点歌剧的味道。正如阿姆斯特丹Muziekgebouw的节目总监Joost Heijthuijsen所言“荷兰是一个同化的国家。约尔丹的居民曾把歌剧改造成符合自己口味的音乐。” 关键在于,观众必须一起合唱。该类型的代表歌曲常围绕爱情、背叛、家庭、法律、囊中羞涩、狂欢派对以及本地小人物的奇闻逸事展开。
如果和任何本地荷兰人聊起levenslied,经过一小时的讨论后,你会发现这个词像一位慈母,包容了庞大而多元的家族。你可以把海盗电台里新鲜、原始的levenslied、狂欢节的节日音乐、以及为溜冰场清扫而演奏的行进乐队音乐,都划分为子类别。商业上的成功也让定义更加宽松一首带有schlager味道的作品可以冲击德国市场;还有的作品采用适合家庭的gabber或R&B元素。
要界定哪些艺术家算是levenslied歌手同样不易。虽然渔村Volendam的歌唱传统与levenslied相似,但并不被视为同类。许多优秀艺术家曾与之“调情”Wim Sonneveld、Robert Long、Ramses Shaffy、Liesbeth List以及伟大的Rob de Nijs都创作过可归入levenslied的歌曲,只是他们在荷兰大众心中更贴近流行榜或歌舞剧。Vader Abraham的《Daar in Dat Kleine Café aan de Haven》(《那座小港咖啡馆》)是典型的“心灵之歌”,但他的代表作《蓝精灵之歌》显然不属于levenslied。
对非荷兰人来说,levenslied的精髓可能像喉音的G一样难以捕捉,但在荷兰它仍然极受欢迎。各类歌单专门收录这个流派官方Spotify歌单“Hollandse Meezingers”(《荷兰合唱》)已有超过15万次收藏,收录了如Marco Schuitmaker重新演绎的永恒金曲《Engelbewaarder》(《守护天使》)等排行榜常青树。如今的levenslied新星Suzan & Freek已经闯入荷兰Top 40。
在Muziekfeest van het Jaar的现场,约有1.7万人中相当比例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反映了像Ammar Bozoglu、Lotje、Tino Martin以及满身纹身、工薪阶层灵魂少年Mart Hoogkamer(可比作莱顿的Marti Pellow)等年轻歌手的号召力。Hoogkamer甚至靠系在裆部的升降装置在观众上方飘荡。年轻歌手的出现也说明,现代levenslied已成为这批年轻人的流行音乐低中产阶级住宅区的生活、郊区烧烤、卧室屏幕时间与睡衣派对的写照。它自豪地保持荷兰视角。当Gerard Joling等老将演唱英文歌曲时,年轻观众往往失去兴趣,留给老歌迷们摇摆。
在热场时,Ziggo Dome的音响系统播放了经典之作《Bloed, Zweet en Tranen》(《血、汗与泪》),由André Hazes演绎,现场观众情绪高涨。Hazes的嗓音足以“叫醒死人”,他在自创歌曲中常扮演英雄旅程的角色痴情的孤独者,或是面对战后重建(wederopbouw)官僚体制的普通人。
《Zeg Maar Niets Meer》(《别再说了》)等金曲充满情感张力。《Bloed, Zweet en Tranen》这首以街头小子视角改编的《My Way》其副歌大意是“用血、汗、泪,我说‘滚开’/用血、汗、泪,我说‘朋友们,后会有期,但游戏结束了’”。Hazes深受大众喜爱,2004年在阿姆斯特丹竞技场的追悼会吸引了5万人现场,另有800万人通过电视观看。
Hazes是一位酗酒且生活多舛的歌手,或许是levenslied最初精神的最后守护者那种不屈且充满灵魂的城市贫民独立精神。类似的精神在Johnny Jordaan 1955年的《De afgekeurde woning》(《被判不宜居住的房子》)中可见“我住在他们称作贫民窟的房子里/但我看不到证据/门上写着‘不可居住’/但对我而言,这仍是宫殿!”
Hazes跨越了两个时代,映射了荷兰从艰苦生活向繁荣转变的轨迹。levenslied的首次盛开发生在1950年代,代表人物包括Johnny Jordaan、Tante Leen、Willy Alberti、Jan & Mien、Manke Nelis以及手风琴手Johnny Meijer。关于Jordaan的影像资料很多,这位在同性恋议题上保持低调的歌手常与表兄Willy Alberti在已消失的酒吧如Café Rooie Nelis里聊天、合唱。少年时期,Jordaan与Alberti打斗失去了一只眼睛,如今两人的雕像矗立在阿姆斯特丹的Johnny Jordaanplein广场。
从80年代中期起,荷兰迎来了自我福祉的高潮,正如Jan Smit的歌曲所唱,举办“一场从Goes到Purmerend的派对”。同样的情绪出现在Mart Hoogkamer的夏季热曲《Ik ga zwemmen in Bacardi Limon》(《我要在百加得柠檬酒里游泳!》)中。曾经描写贫困与家庭困境的歌曲,如Zangeres Zonder Naam 1959年的《Ach vaderlief, toe drink niet meer》(《亲爱的父亲,请别再喝酒》),已让位于轻度放纵。去年去世的René Karst以“宁可肥到装不进棺材也不缺派对”“周六我从一包薯片和一支全烟开始”之类的豪放歌词,彰显其享乐主义人生观。
许多经典levenslied歌曲都有一个knipoog(“暗讽”)时刻,如Jordaan对自己贫民窟公寓的自嘲。如今的knipoog更倾向于描写无害的调皮Frans Bauer唱起请假一天、在窗台摆上一束新鲜花的情景。一些现代曲目甚至相当挑逗在一首快节奏歌曲里,电视主持人Gerard Joling邀请情人“用你的手指和舌头把我弄疯”。
有人认为,levenslied已经不再是底层自发的工人阶级现象,而是被主流媒体所主导的产品——Muziekfeest van het Jaar取代了昔日的酒吧Café Rooie Nelis。虽然一些新歌仍先在被称为piratenmuziek的非官方网络传播,但近年来主流电视选秀节目往往决定谁能走红,而非本地酒吧的自发创作。新作品多赞美温柔的恋爱关系,听感与1974年Corry Konings的轰动金曲《Huilen is voor jou te laat》(《为你哭已太迟》)相去甚远——后者是一首讲述女子对前任狠心回击的歌曲。
当Ziggo Dome内的演出渐入高潮,烟火、舞女、干冰以及不断捕捉观众的“亲吻摄像机”交相辉映。面对如此宏大的场地,歌手们夸张舞台形象或是调皮的情场浪子,或是火辣的女歌手,亦或是深情却被误解的局外人。他们在聚光灯下深情对唱,或从舞台下方、甚至观众席的隐蔽处出现。观众随音乐摇摆、交谈——这不是失礼,而是符合古老节庆与狂欢传统的热情参与。事实上,我们甚至会被带回过去在一次体现荷兰高效时间观念的环节中,大家与活泼的主持人一起倒数迎接2026,新年不留空白。
尽管灯光炫目、表演华丽,这依旧是一个充满欢乐与感动的夜晚。Senna Willems的表演便是这种柔化硬朗风格的典型例子。她是一位声音温暖、气质自然的歌手,因电视选秀《We Want More》走红。当晚她献上了《Je Hoeft Niet Altijd 6 Te Gooien》(《你不必总是投出六点》),开场以酒吧钢琴前奏引入,随后与观众合唱《Kleine Vogel》(《小鸟》),大屏幕上播放的官方MV甚至暗示一只被老Twitter小鸟绑架的Senna木偶。无论如何,观众随之摇摆、鼓掌——gezellig,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