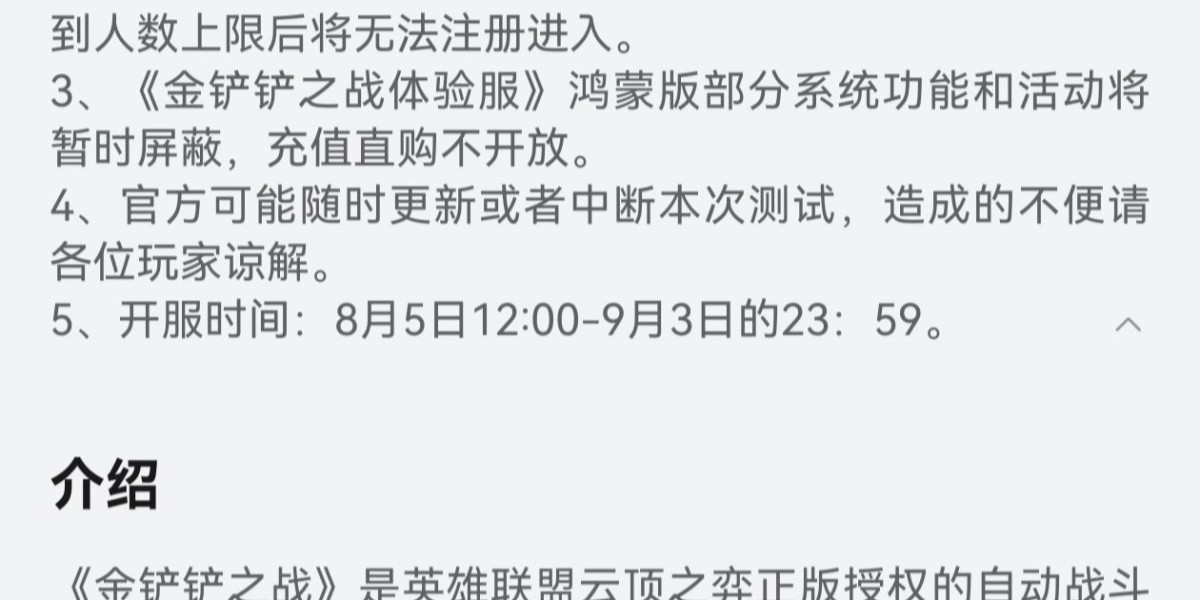小区门岗的小屋里,时常坐着老谢。
70多岁的老谢,脸上满是皱纹,每一道都刻着生活的沧桑;一口牙被经年累月的烟和浓茶熏得发黑,那是岁月留下的印记。
冬天的他,常戴一顶鸭舌帽,裹一件长及小腿的深灰色羽绒服,料子被时光磨得发亮,像被生活细细盘过的包浆。肩上斜挎着一个泛黄的粗布包,边角磨得发白,带子被汗水浸得有些发硬,里面永远揣着那个脱漆的不锈钢保温杯,泡着酽酽的热茶。
他上的是隔天班,一班就是24个小时,从清晨守到深夜,再从深夜熬到次日天光,通宵蜷在小屋里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椅上,手边一壶茶,手机刷着抖音,偶尔跟着哼几句老歌。
《林海雪原》里杨子荣的唱段是他的拿手好戏,调子不准,嗓门还带着几分沙哑,每当我路过时,听到老谢在唱歌,就知道他今天心情不错。
老谢的人生,算不上顺遂。年轻时他也曾揣着一腔热血,点灯熬油地读书,盼着能考个好前程,奈何家里太穷,终究没能把书读下去。旁人都说他是读书的苗子,可惜了,他却转头学了砖工手艺,一把砖刀耍得炉火纯青,靠着这门手艺走南闯北,硬是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老谢爱喝早酒,酒后自述的人生阅历,总有些零碎,容易断篇。
二三十年前,他跟着同乡到外地去砌砖,那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高光时刻。他说,当时坐着绿皮火车咣当咣当晃了好几天才到,那边砌砖的收入还不错。只是那里的冬天来得早,一年也就3个月的活儿,6月份过去,9月份就得往回赶。
挣了钱的老谢,回程时大方地坐了一次飞机,那趟云端上的路,成了他念叨的谈资。
后来,他又去了另一处,凭着做事有计划、安排有条理的劲头,当上了小班组长,带着一个班组的人砌砖盖房,工期从不出错,工人们都服他。
聊起当年的砖工生涯,老谢总唏嘘,说有个工友被飞溅的砖屑崩到眼睛,最后落了个眼瞎的下场,自己做了这么多年,没出过半点岔子,已是天大的幸运。
那时候的日子苦,白天抡着砖刀跟砖块较劲,浑身累得散了架,晚上就凑着工友们喝两口小酒,扯着嗓子唱几段歌,不为别的,就为借着这股子热闹劲,把一身的疲惫都松快下去,这唱歌的习惯,也就这么跟着他过了大半辈子。
在小区值班结束后,老谢能踏踏实实地歇一整天。等歇透了,就挎着那个黄布包出门逛。有时散步遇上他,我便陪他走一段,听他讲那些旧日子。
因为每次都喝两口小酒的缘故,说着说着他就有点凌乱,不能完整地叙述,让人听得云里雾里。大意是:要是能读上书,就不会像现在的样子。还说当年要是再攒点钱,说不定能做点像样的事。牢骚归牢骚,转头他又会亮开嗓子哼起《林海雪原》的唱段,末了还拽着我的袖子,非要教我几句,那笃定的模样,仿佛只要他肯教,就没有教不会的道理。
有人问他,熬24小时的班累不累,一辈子没做成啥“大事”,会不会觉得遗憾。
老谢呷了口茶,慢悠悠地说:“《中庸》里讲‘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人这一辈子,哪能事事都遂心?年轻时拼过了,挣过高薪,坐过飞机,还带过班组,就不算亏;老了能守着一碗茶、一段歌,安安稳稳过日子,就挺好。”这话一出,旁人都暗暗称奇,谁能想到一个砖工出身的老保安,竟能把这般深奥的句子记这么牢,足见当年读书时的底子。
老谢的日子,过得像他杯里的茶,初尝带点涩,细品却有回甘。上班时守着一方门岗小屋,看遍小区的人来人往;休息时逛遍街巷的烟火寻常,念叨唱腔里的门道。
《菜根谭》里说:“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老谢或许没读过这句话,可他活成了这个样子。年轻时奋力追梦,纵使未成,也不曾怨怼;年老时安于寻常,守着一茶一歌,把柴米油盐过成了诗。
其实,我们大多是老谢这样的普通人,没有光环加身,没有传奇可讲。可人生的真谛,从来都不在轰轰烈烈里,而在那些妥帖安放的日常里——一壶热茶,一段老歌,一次散步,一句牢骚后的释然。
老谢的日子,更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生活的模样:努力过,便不悔;安顿好,便是福。而在我们身边,无数个老谢的人生,就像小区外面道路上的黄葛树叶,绿了又枯,枯了再发,春有生机,夏有荫凉,秋有金黄,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