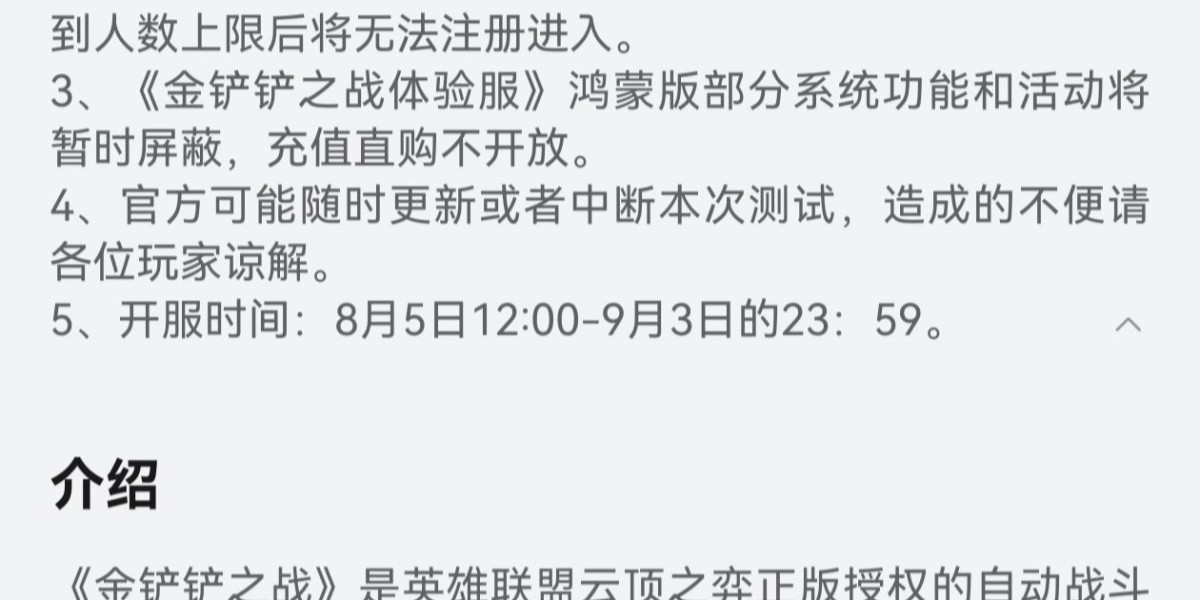那种房子走廊长长的一眼望不到头,每家门口都摆着煤炉子、自行车和各种杂物,炒菜的油烟味儿混着邻居家孩子的哭声,一天到晚都热闹得不行。后来小学四五年级,我们家搬到了北新桥这边,原先是明末时候的王承恩府,说来也巧,那位王承恩公公当年是崇祯皇帝身边最信任的人,可惜历史翻篇后,这地方早就没了当初的模样。我第一次见到它时,满眼都是热火朝天的大工地,推土机轰隆隆响个不停,灰尘漫天,谁能想到几百年后,这里会变成我们一家人最熟悉的家呢。
九十年代初,大院里接连盖起了五栋六层单元楼,我们家属于第一批搬进来的住户。院子门口有个传达室,早晚都有人守着。晚上九点多,铁栅栏大门咔哒一声就锁上了。那时候私家车还很少见,大多数人上下班靠两条腿或者挤公共汽车,晚归的人只能从传达室旁边的小铁门进出。守门的钟大爷特别有派头,嗓门洪亮,眼神跟鹰似的,性子也急,谁家孩子淘气跑出大门,他老远就能喊住。平时他捧着一大瓷缸浓茶,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一会儿跟张婶聊两句菜价,一会儿又跟李叔吐槽单位的事儿。院里谁姓什么、住几号楼、家里谁在哪个科室上班,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就跟一本活户口本似的。
信件和报纸也都在传达室登记,钟大爷用粉笔在门口小黑板上写收件人名字,谁路过看见了就自己去拿,拿完再把名字擦掉。那块黑板每天早上都写得满满当当,像个小型公告栏。谁家订的《北京晚报》到了,或者外地亲戚寄来的信,大家伙儿互相提醒,生怕谁漏了。这样的小事,现在想想挺琐碎,可当时就是大家伙儿生活的调味剂。谁要是好几天没见人影,钟大爷准会嘀咕一句,这家子是不是出差去了?邻里之间这份熟悉劲儿,是现在很多高楼小区里再也找不回来的温度。
楼房虽然新盖,可设施还带着浓浓的单位时代痕迹。每家都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了,但热水还是得去打。每天清早,我妈就塞给我一个大暖瓶,让我去食堂门口排队打开水。锅炉房里蒸汽呼呼往外冒,师傅们用铁锹铲煤,汗水把工作服都湿透了。大家排着长队,有说有笑,谁家暖瓶漏水了,前面的人还会帮忙扶一把。澡堂子每周开放两个下午,免费,谁都能去。我常约着院里几个小伙伴,一起拎着盆、毛巾、香皂、洗发水和换洗衣服,浩浩荡荡地杀过去。路上总有人忘带东西,到了澡堂门口又得折回去取,常常闹出笑话。可每次泡在热腾腾的大池子里,听着水龙头哗哗响,身上灰尘一冲而光,那种舒服劲儿真是没法说。
澡堂子里不管是普通职工、领导还是家属,一律平等。没听说过给谁单开小灶或者雅间,大家光着膀子聊天,聊孩子学习、聊单位奖金、聊菜市场今天黄瓜多少钱一斤。那种不分高低贵贱的氛围,是那个年代最朴实的人情味。现在有些地方讲究分层消费,领导有专属休息室,普通人只能排队等位,想想都觉得隔得远了。你有没有想过,当年大家洗澡都挤一个池子,到底是因为条件有限,还是因为人心还没那么复杂?
外公外婆单位就在院子门外胡同两侧,中午下班,职工们呼啦啦全涌进大院食堂吃饭。外公是食堂炊事班长,厨艺好,脾气也倔,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沾着他的光,我每天放学都能溜进后厨玩。可外公原则性强,除了刚出锅的窝窝头或者叉烧包,其他东西碰都不让我碰。食堂房子特别大,房顶高高的,能坐两百多人。周末中午吃完饭,这里常常免费放电影。门都不用票,胡同里的老街坊熟门熟路就跑来,我们这群小孩更是疯得不行,抢着坐第一排,爆米花撒一地,笑声能把房顶掀翻。
大院最里面还有个更专业的影视厅,属于中国新闻社的办公楼。近水楼台先得月,刘晓庆早期的电影,我就是在这儿免费看的。逢年过节,这里还办交谊舞会,职工家属都能来跳舞。灯一亮,音乐一响,老的少的都下场,笨手笨脚的也跟着扭,笑成一团。那时候跳舞可不是什么高雅事儿,就是大家伙儿找乐子,放松一下。
院里孩子多,还有一批比我小的。为了解决双职工没人带娃的问题,单位把一个小园子改成了托儿所,请退休的老职工帮忙看着。老人家耐心好,会讲故事,会哄睡觉,我们放学了也爱跑去凑热闹。这样的日子,简单却踏实,大家像一家人。
前两年我回去看过一次。大院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外公单位搬走了,楼房外墙刷成了灰色,像老北京四合院常见的颜色。小卖部拆了,食堂关门了,院里停满了私家车,晚上大门也不锁了。很多老邻居把房子卖掉搬走了,新来的大多是年轻人,北漂一族。他们或许刚毕业,或许拖家带口,在这里落脚,追梦,磕磕绊绊地开始新生活。也许某天晚上,他们也会在楼道里闻到邻居炒菜的香味,也许会在传达室旧址的位置发呆,也许会在某个周末想起,这里曾经有过一群人,一起打水,一起洗澡,一起笑,一起闹。
时代变了,生活方式变了,可人心里那份对温暖、对邻里、对简单日子的向往,从来没变过。那些年,我们没有很多钱,却有满满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现在物质丰富了,高楼林立了,可偶尔深夜想起当年大院里的灯光和笑声,心里还是会软一下。生活到底是什么?大概就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常,拼在一起,成了我们最珍贵的一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