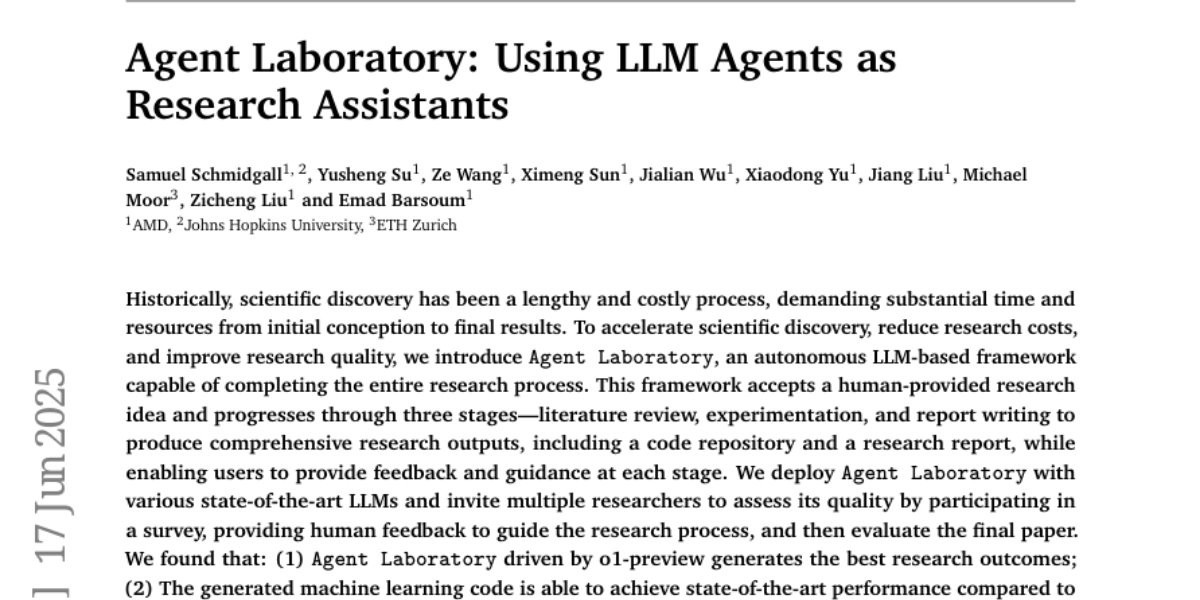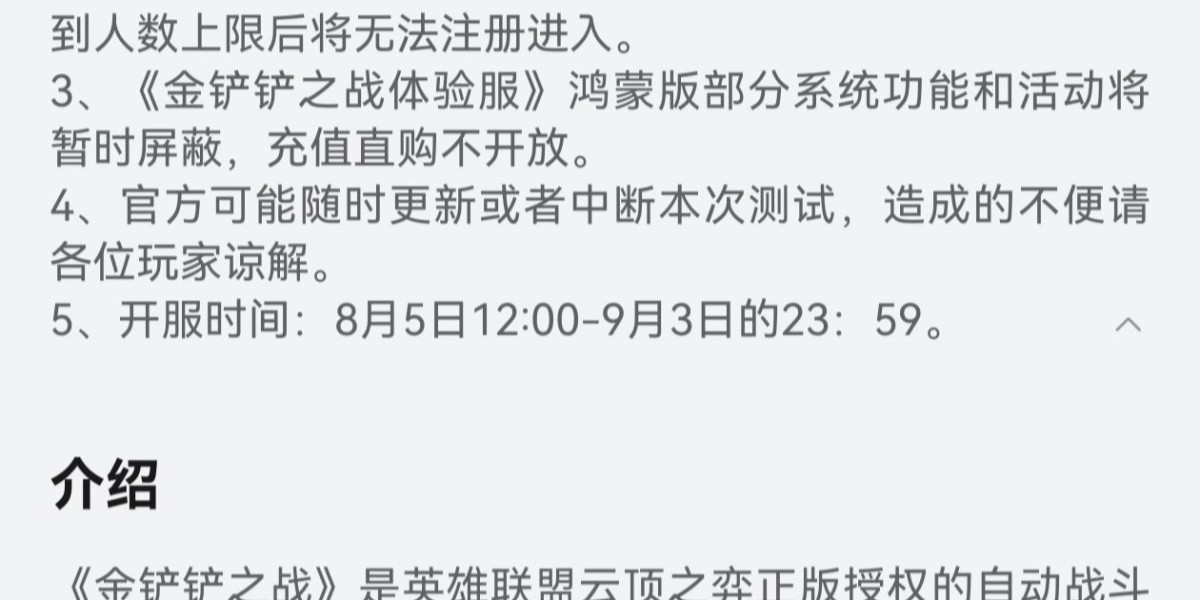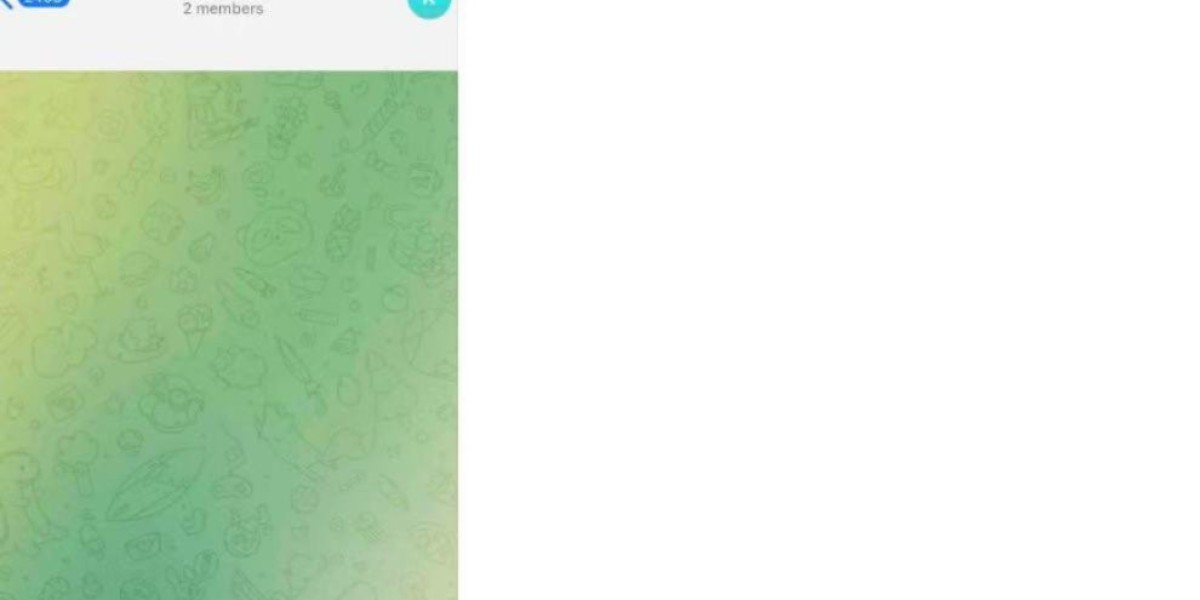德国文学研究者莱纳·施塔赫具有历史的宏观视野、文学的敏锐见地,以及人之为人的体贴。因此,他为卡夫卡所做的传记足以把传主放置在真切、鲜活的广阔时代背景中,又不失对卡夫卡那些独异文学作品的理解,而更重要的是,他尽力从“人”的角度去体贴另外一个人,即卡夫卡,努力感知其感知,感受其感受。如此书写出来的传记,必然是极丰富且保存着热度的。在《卡夫卡传:早年》和《卡夫卡传:关键岁月》之后,如今,《卡夫卡传:领悟之年》出版,《卡夫卡传》显现出全貌。
卡夫卡,1922年。
《领悟之年》从1916年开始写起,直至卡夫卡去世的1924年。在生命最后的八年,卡夫卡一如既往关注着他的内在世界,写出《城堡》《饥饿艺术家》等最重要的作品,但他也必须面对外在世界的大动荡,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仍寻觅着拯救,还幸运地遇到了爱情,但最终,疾病把他的生命停止在四十岁零十一个月。本文摘自《卡夫卡传:领悟之年》的最后一章,讲述了卡夫卡生命的最后时光。
《卡夫卡传:领悟之年·1916-1924》
作者:莱纳·施塔赫
译者:黄雪媛 程卫平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纪念碑
2026年1月
卡夫卡的最后几个星期无异于煎熬。并不是所有肺结核患者都会像文学作品常常描写的那样在亢奋中死去,他们的结局可能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这一点他在马特利亚里就有了解,当时他目睹了隔壁患者的惨状,在那之后,他就央求年轻的克洛普施托克答应他,与其那样人为地延长煎熬时间,不如给他注射吗啡。他最近在维也纳医院的经历让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情况可能比那位最终从火车上跳下去自杀的病友更糟糕。
尽管每个医生都做出了大致相同且令人沮丧的诊断,克洛普施托克还是请了哈耶克教授来基尔林,四个星期不见卡夫卡,其身体组织破坏之快令哈耶克大为惊讶。他和贝克医生一样,想通过注射酒精来封闭喉上神经。结果,收效不大。卡夫卡现在经常要打这种针(他希望没旁人在场),非常难受,可不打又根本不行:喉部的轻微活动都会引发刀割般的疼痛,咳嗽更是煎熬。就连喝水也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他经常感到口渴,做梦梦到各种各样的饮料,他喜欢看着别人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光一杯水。他每天逼着自己喝一小杯葡萄酒,有时候喝一点点啤酒,水在喝之前还得先加热。“你也尝过今年新酿的葡萄酒吗?”他问父亲,“我真想什么时候跟你一起大口大口地喝上几杯,虽然我酒量不大,但论口渴我可是不甘人后的。这样我就释放了我的酒客之心。”这些玩笑话刚说完一两天,卡夫卡从克洛普施托克那里得知,他现在必须靠别人喂食才可能活下去了:“这一措施令他绝望,”克洛普施托克在信里写道,“我甚至都没法跟他说,精神上他很难接受。”
“他其实非常需要尊重。”朵拉后来在谈到卡夫卡时写道,“如果你很尊重他,一切都好办,他并不在乎什么形式。但如果没有得到尊重,他就非常恼火。”她的话有助于解释卡夫卡某些出人意料的生硬态度:即使他把自己贬得一无是处,也绝不允许别人当他不存在。但卡夫卡的怪脾气也有同等重要的另一面:他意识到自己也必须赢得这种尊重,这种意识在他身上至死都没有消失,他很怀疑,一个四十岁的人,一个不再具有最自然的反应能力、必须靠别人喂食方可维持生命的人,究竟能否展现令人尊敬的形象。
他的脑力工作能力也是如此。卡夫卡早已接受他的储备正在消减的事实。疾病、虚弱、强忍疼痛、在恐惧与希望之间的挣扎,这一切令他疲惫不堪。“紧闭是我眼睛的自然状态,”他在给布罗德的信中写道,布罗德刚给他寄来几本雷克拉姆出版社的书,“但是跟书和报刊游戏令我快乐。”因为内心非常抵触,韦尔弗的长篇小说《威尔第》他读得极慢,他还是更喜欢翻阅家人定期给他寄来的《布拉格日报》。他很感激朵拉和克洛普施托克接手了他的大部分日常通信;但是,药物对心理的副作用却让他不安。他指出:“即便我真能从这种种举措中恢复一点点,我也肯定不会从麻醉剂中恢复过来。”他尤其厌恶酒精注射,注射的间隔时间还越来越短,没完没了,会使他的思维变得模糊,影响他的表达力:人们可以尊重一个疲惫不堪的人,甚至也可以尊重一个被医生判定缄默的人,却不能尊重一个被注射了酒精的人。卡夫卡偶尔甚至会想,他宁愿承受疼痛,也不愿失去控制乃至自尊。
卡夫卡画作。
他焦急地等待着《饥饿艺术家》小说集的校样:毫无疑问,只要卡夫卡的意识还清醒,他便像以前那样一丝不苟,独自完成校对、修订工作。布罗德以卡夫卡病情危急为由,敦促出版商尽快排版,但“铁匠铺”仍在等待《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他们得知这是第四个中篇小说。终于,在5月中旬,卡夫卡收到一校样。此时,他的体力早已大不如前,白天也经常昏睡。“现在我想读一读,”他说,“也许它会惹我过于激动,因为我必须重新体验它。”卡夫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自己的文本产生类似恐惧的感觉,特别是其中的标题小说《饥饿艺术家》。小说讲的是一个不想再吃东西的人,但它却是由一个不能再吃东西的人所写。卡夫卡在作品里经常使用食物和绝食的隐喻,所以这种残酷的悖论更令他难以承受,他在读校样的时候难掩泪水,就连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卡夫卡费尽心血的克洛普施托克也觉得当时的情景“非常恐怖”。即便如此,卡夫卡仍坚持通读了5月下旬送达的终校样,去世前一天他还在校对。
他似乎拒绝在精神层面“打折扣”,即使面对将至的死亡,他也竭力保持认知力的高度,抱持一种在智识上不失体面的态度。谈话记录清楚地显示,他对那些毫无事实依据的安抚和鼓励并不买账:“我们总是这么谈我的喉咙,”他写道,“就好像它只会好转似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还有一回,他说:“如果说我现在摄入的食物量不足以让我的身体从内部复元,这是真的话——很可能是真的,那么确实毫无指望了,除非发生奇迹。”有次,克洛普施托克弄断了一片压舌板,卡夫卡说:“倘若我能活下去,您还会在我身上弄断十片的。”当然,克洛普施托克向他保证,他一定会活下去的,卡夫卡回答:“这话我想听,虽然我并不相信。”
卡夫卡渴望得到安慰,任何人面对这种情境都会如此;到5月中旬,他的求生意志仍未崩溃,哪怕一丝真正有希望的迹象都令他激动不已,甚至会一时忘记自己的病情。他说:“在我吃东西的时候,开始感觉到喉咙里有什么掉落下去,这让我感到无比自由,我立刻想到各种可能发生的奇迹,但这感觉马上又不见了。”奇亚斯尼教授每个星期来基尔林一次,有一回他竟发现卡夫卡的喉咙比上次好了一些,很是惊讶。朵拉走进来的时候,卡夫卡泪流满面,他一次又一次拥抱她,说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生命和健康。“我们什么时候去做手术?”一张便条如此写道,也说明,5月的时候,卡夫卡仍相信手术可以缓解病情。
这只是些偶尔闪现的乐观瞬间。大部分时间,他认识到未来(他在最后的声明中没有提及未来)的前景正在关闭,无法阻挡。大部分时间,他感到恐惧:不是对生命终结的恐惧,不是对进入未知幽暗的恐惧,而是对充满痛苦的死亡过程的恐惧。痛苦的死亡在逼近他,卡夫卡心里明白,虽然跟他交谈的每个人都刻意回避这个话题。但是,诊断结果确凿无疑,卡夫卡在维也纳医院观察到的情况也同样无可置疑。喉部水肿,尤其是声门部位水肿意味着窒息而死。如果他不愿再次接受哈耶克教授的治疗——即不可避免的气管切开术,他会在基尔林窒息而死。
最亲爱的父母,现在说说你们几次在信里提及的探视吧。我每天都在想这事,因为对我非常重要。你们来该多好啊,我们已经很久没在一起了——不算和你们在布拉格的那几天,当时只搅得家里不安宁——我指的是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咱们安安静静在一起待上几天,我压根都不记得上回在一起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那回在弗朗齐歇克温泉镇,咱们待了几个小时。然后,就像你们在信里写的,“喝一杯上好的啤酒”,从这句话我看得出,父亲对今年新酿的葡萄酒并不看好,而就啤酒而言,我也同意他的看法。另外,我现在碰到热天就常常回想起,我们俩以前也经常一起喝啤酒的,是在许多年前,父亲带我去市民游泳学校的那段时间。
刚才这一点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都支持你们这次出行,但反对的因素就太多了。首先,父亲很可能因为护照问题无法成行。这自然会削减此行的很大一部分意义,而最关键的是,这样一来,不管是谁陪母亲过来,她都会把太多注意力引到我身上,会过于关注我,而我现在样子还不太好,根本没什么可看的。在维也纳的时候,以及在这里刚开始那段时间的一些问题,你们也都是知道的,这些问题导致我体质下降,影响了快速退烧,结果又进一步削弱了我的体力。喉部问题在开始的时候对我刺激很大,那种打击对我体质的削弱甚至超过病情实际应该造成的影响——到现在,我才在朵拉和罗伯特的帮助下(没有他们我可怎么办!)从所有这些削弱我体力的因素中挣扎出来,他们的帮助是你们在远方完全无法想象的。不舒服的地方还是有一些的,比方说,前几天得了肠炎,现在还未痊愈。这一切共同发生作用,结果就是,尽管我有好帮手,尽管这里空气优良,吃的也很不错,几乎每天享受日光浴,我还是没有完全调养好,总体上甚至还赶不上前不久在布拉格时的状况。此外还要考虑到我现在只能轻声耳语,即使耳语也不能多说,所以你们应该不会介意推迟来访。一切都处在最好的开端——最近一位教授诊断说,我的喉咙有了明显好转,虽然我[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位和善、无私的人——他每个星期自己开车来这里一次,而且几乎不收任何费用——但他的话还是给了我莫大安慰,正如我所说的,一切都处在最好的开端,但即使是最好的开端也没有什么结果;既然我不能向来访者——更何况是像你们两位这样的来访者——展示无可否认的、连外行人用眼睛都能看出来的重大进展,那我想还是算了吧。所以,亲爱的父母,咱们要不暂时还是算了吧?
卡夫卡在去世前一天写的这封信。他完全掌控着局面,直到最后时刻,他仍能自如调用他生命的媒介——语言。他想要和解,甚至跟父亲和解,他的思想停在过去,集中在记忆里为数不多的闪光时刻,他也跟朵拉说过,他曾经和父亲一起喝过啤酒。但为了让他实现和解,必须给他安宁。关于母亲来探视的问题以前就谈过了,但现在,父母来信说他们俩都想来。原因是他想不到的。尤莉叶·卡夫卡向克洛普施托克询问她儿子的诊断结果,克洛普施托克回以沉默。
朵拉,卡夫卡女友。
卡夫卡肯定跟朵拉讨论过父母探视的问题。让他父母住疗养院的客房,想想就可怕。或许,他们可以把这次出行当成避暑,在附近找家旅馆住下,出门游览,顺便每天来一趟疗养院?卡夫卡差点接受了这个想法。但是冲击还是太大——不仅对他自己,对父母也一样,而他们难免会将这冲击反映给他。不行,这行不通。“一切都处在最好的开端。”
1924年6月2日,星期一,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卡夫卡躺在阳台上,审读他最后一本书的校样。过了会儿,克洛普施托克从维也纳回来,买了些东西:草莓,樱桃。卡夫卡闻着这些水果的清香,一遍又一遍,然后才慢慢吃起来。随后,他开始给父母写信。信越写越长,他太累了,无法写完。“我从他手里接过信来,”朵拉在同一页信纸上补充道,“他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剩几句话了,但按他的要求似乎非常重要:”然而,在冒号之后便什么都没有了。也许,他睡着了。
翌日,也就是6月3日,那天的事,只留下间接的信息:克洛普施托克传达了一些信息,布罗德写进了他的卡夫卡回忆录,还有一位护士的口述报告,由威利·哈斯记录下来。这些回忆不乏相互矛盾之处,但也相互补充。
凌晨四点,朵拉匆匆跑到克洛普施托克的房间,叫醒他:卡夫卡呼吸困难。克洛普施托克穿上衣服,看了一下他的朋友,连忙通知了当晚在疗养院值班的医生。医生给卡夫卡注射樟脑,刺激呼吸中枢,并在他喉咙上敷了冰袋。但都无济于事。卡夫卡呼吸急促,疼痛不堪。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
上午,某个时刻,卡夫卡粗鲁地示意护士离开房间。接着,他要求克洛普施托克注射致命剂量的吗啡。“四年来,这是您一直许诺我的。”几个星期以来,克洛普施托克一直害怕这个职责,他表示反对。此刻的卡夫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别人的决定,他突然凶起来,指责克洛普施托克若不履行这最后的职责,那他就是杀人犯。“您在折磨我,一直都在折磨我。我不会再跟您说话。我会自己去死。”克洛普施托克给卡夫卡注射了潘托邦,一种鸦片剂,麻痹作用几乎不亚于吗啡。卡夫卡还是不信他——“别骗我,您给我的是专用药!”但当他感到疼痛减轻,就要求再注射一点。克洛普施托克又注射了些,具体多少,我们不得而知。
他们找了个借口把朵拉支到镇上去了,这样她就不必目睹这场挣扎了,这是卡夫卡和克洛普施托克约好的。但在卡夫卡弥留之际,他又想她了,于是派了一个女仆把朵拉接了回来。她跑来了,气喘吁吁,坐在卡夫卡床边,跟他说话,把几朵鲜花捧到他面前,让他闻。卡夫卡,看似已经失去意识,那一刻竟最后一次抬起了头。
卡夫卡画作。
卡夫卡去世时四十岁零十一个月。在犹太社区的死亡登记簿上,死亡原因写的是“心脏骤停”(Herzlähmung)。西格弗里德·勒维和卡尔·赫尔曼赶到基尔林,办了相关手续。两天后,卡夫卡的遗体被装入金属焊接的棺材,运往布拉格;火车上,跟克洛普施托克、勒维、赫尔曼同坐一节车厢的,还有朵拉·迪亚曼特,这将是她第一次踏上卡夫卡的故乡。卡夫卡的父母和几个妹妹给予了她应有的接待。“只有认识朵拉的人,才能明白什么叫作爱。”卡夫卡去世那天,克洛普施托克在给艾莉的信中如此写道。
随后几天,布拉格发了几篇讣告,都是卡夫卡生前好友写的:马克斯·布罗德发在《布拉格日报》上,鲁道夫·福克斯(Rudolf Fuchs)发在《布拉格晚报》,奥斯卡·鲍姆发在《布拉格报》,费利克斯·韦尔奇发在《自卫》,密伦娜·耶森斯卡发在《人民报》。所有人都震惊不已,为表达失去好友之痛,他们搜寻各种溢美之辞,以高扬的声调,在称颂逝者的惯例里自我救赎。
卡夫卡被安葬在布拉格郊外斯特拉什尼采(Strašnice)的新犹太公墓,离老城区几公里远。犹太葬礼仪式于6月11日举行,在下午四点左右,天气闷热。参加葬礼的人不足一百人,布拉格的政治、文化机构没有派代表来,无论是德裔的还是捷克裔的。
八天后,也就是6月19日,布拉格德意志室内剧院举行卡夫卡追思会,由马克斯·布罗德和布拉格德意志剧院戏剧总监汉斯·德密茨发起。剧院里座无虚席。布罗德和二十八岁的作家兼记者约翰内斯·乌尔齐迪尔先后发言。接着,一位演员朗诵了卡夫卡的作品,包括《一个梦》《在法的门前》和《一道圣旨》。
乌尔齐迪尔讲的话流传下来,因为他在会后不久公开发表了悼词。他见过卡夫卡几次,并在较大文学圈聚会的咖啡馆观察过他。他的悼词没有透露一点亲密的私人关系,倒是出现了诸如“内心真实的狂热追求者”“高尚而单纯的作家”“奇异的天才”之类的套话。不过,悼词里有句话值得注意,乌尔齐迪尔可能是卡夫卡身后第一个提醒大家注意这一关键问题的人:“如果真有那么一个例子证明生活与艺术可以完全重合的话,那就是弗朗茨·卡夫卡。”
后来,乌尔齐迪尔在回忆布拉格德语文学界时又回到这一问题,即“完全重合”之谜。他写道,卡夫卡的文字格外“深”,这是卡夫卡所有朋友的一致看法,无论他们的判断是基于文学,如马克斯·布罗德、奥斯卡·鲍姆;还是基于哲学,如费利克斯·韦尔奇;抑或是基于宗教史,如胡戈·贝格曼。但他们都在徒劳地寻找最后一道门的钥匙。“他们顶多知道如何解释卡夫卡可能要表达的意思,读者可能认同他们的解释,也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见解。然而,这是如何发生的——卡夫卡如何说出他所说的话;他如何以他的方式说出他的话;我们如何做到从未与他所说的或他本人发生直接冲突;这些,他们中间没人能解释明白。”
那是如何发生的。应该从这里开始。
作者/莱纳·施塔赫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