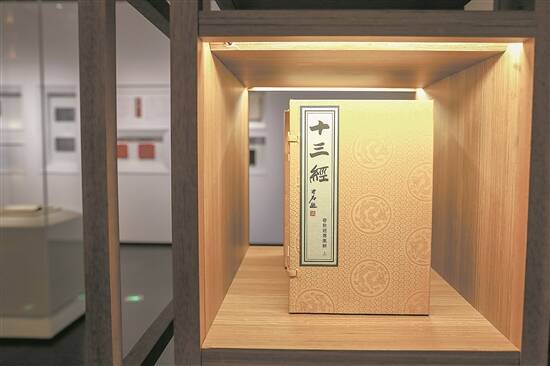本文转自:羊城晚报
| 线装书《十三经》,拍摄于扬州非遗珍宝馆 视觉中国供图 |
□李震
西哲有名谚曰:哲学是一种总在自我拆台的工作。如果从更正面的意义上理解,我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哲学作为一种根源性学问,它的进步总是在自我否定的重建中展开。重建就是要不断向下深挖学科的地基,以求更贴近这个世界的真实。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重建,追求的就是更加通达中国文明所理解的世界真实,而不是别的什么其他传统或者自称无传统者所理解的真实。这是一个更加深刻地把握传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更加主动地导引未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强化自我而非抽空自我的过程。经史传统,就是我们现在研究中国哲学希望开掘的新地基。
我把经史传统作为中国哲学研究视角的价值理解为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关涉于固有的研究范式而言的。
其一是找回理解自我的框架。
20世纪以来,由前辈学者确立的中国哲学史书写的经典范式,呈现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脉络和研究进路,这是中国哲学学科的共法,其方法与价值必须得到充分继承和肯定。当然这套范式也不是没有缺陷,缺陷之一就是理论框架有时稍嫌外在、拘定,与理论对象不尽贴合,难以处理框架之外的问题。
分板块来讲,形上学、心性论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一般的哲学史写作处理相对成功的部分;工夫论、认识论、伦理学、历史或政治哲学虽然也被认为重要,但处理常常不太出彩。至于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中国文明自身的理论框架和演化规律——这很接近我们今天所谓的经史问题——因为在板块之外,就很少会被纳入讨论的范围。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学科自创建之日起,就较多地依赖于对西方哲学分科结构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中形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的三分法)的仿效而较少建立起中国文明自我的哲学性认知。这就导致:不仅对于那些中国文明里比较独特的内容,如工夫论、历史观,我们缺乏有效的分析框架;即使是面对中国文明里那些看起来最能跟西方通约的部分,比如形而上学,我们实际上往往也是在借助西方概念、西方逻辑而不是足够本我地来理解自身。这样简单格义比附的做法到了一定的深度,就一定会发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错误。对这一点,我们很多时候还缺乏足够的自觉。
改变这种现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找回理解自我的框架。找回自我不是简单复古,而是要重获内生地认识世界的能力。经史传统有两点很重要的内涵,有助于我们处理这个疑难。第一,经史传统主张把思想放回到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整体背景和经典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中去理解,给中国思想提供了一个理解自身的内在语境。第二,经史传统不是去寻找一个所谓客观、最初、不变的本我,而是在流变中去整体地把握一个不断展开的传统,把中国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能动的、自我展开的主体,用张志强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在源流互质中认识自我。从这样的角度出发,那些难以处理的、被漏掉的问题,可能会得到更切己的认识。所以经史传统在我看来是规避既有框架的刚性缺陷、展开新的理解可能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其二是增强解释历史的力度。
既有的中国哲学史范式最擅长处理的是静态的、横截面的概念分析,但在动态的、纵贯性的历史线索勾连上常常显得费力,不太好回答思想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思想流变的脉络线索——无论面对的是个体思想还是一个时段的思想,都是如此,这部分解释常常有点硬加上去的感觉。我想归根到底,这是因为既有的框架往往不是从具体历史中提炼出来的,而是把一套普适的方式应用到具体历史之上,希望用一个万能的公式解决所有问题。经史传统的特殊之处,某种意义而言,我觉得恰恰是在“史”上,因为史是真正的具体性,是对过分外在框架的克服。所以我理解的经史传统一定是经史并重,一方面要以经统史,认识到经当中蕴涵的大经大法;另一方面也要以史统经,因为只有史才能说明思想的转换,才能解释变化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以史统经,进而统摄整个经、子之学,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真正具体地、实事求是地回到思想的历史语境,找到思想自身流变的历史轨迹,经学、子学和专门的史学则是我们在这一宗旨下可以切入的具体抓手和途径。
以上两点是我所理解的经史传统视角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为传统的哲学史研究作个辩护。哲学史研究真的不重要了吗?当然不是。对此至少可从经与史的角度作两种不同的说明。从史的角度来说,哲学史也是史,对于史的肯定必须把哲学史也包含在内,经史问题不能脱离思想流变的历史得到理解。从经的角度来说,虽然哲学史研究传统上常被当作子学看待,子学好像总是独立于经学之外的一家之言,但其实经与子是辩证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子部的作品随历史变迁可能会具有类似新经的地位,比如《太极图说》《通书》《西铭》这样的文献,在理学时代其实获得了比肩经书的尊崇,钱穆先生就是立足于这一点而提出所谓“新七经”的论断(钱穆先生的范围拓展得更宽,把道家和佛教也纳入了进来);而且是因为,历史上的那些被称为子的哲学家,他们自己真实的志向其实从来都不是在经典之外“立一家之言”,相反,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真正讲出了经典的精义,他们毕生所志其实是以作传的方式来明经,他们写的那些论说性文字在根本上往往有《易传》式的自我期许。这就是说,《易传》是对于《易经》的阐释,假如没有《易传》,《易经》甚至难说讲出了什么系统的哲学,《易传》才是《易经》的精蕴;类似地,其他经典当中的深义,也要有待于历代的哲学家提炼、阐明、发挥,才能成为时代的思想精华。在这个意义上,诸子或哲学家是真正激活、点化了经典的人,是经典和传统的担纲者。我们对于哲学史的肯定,也正是以这一点为核心的。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