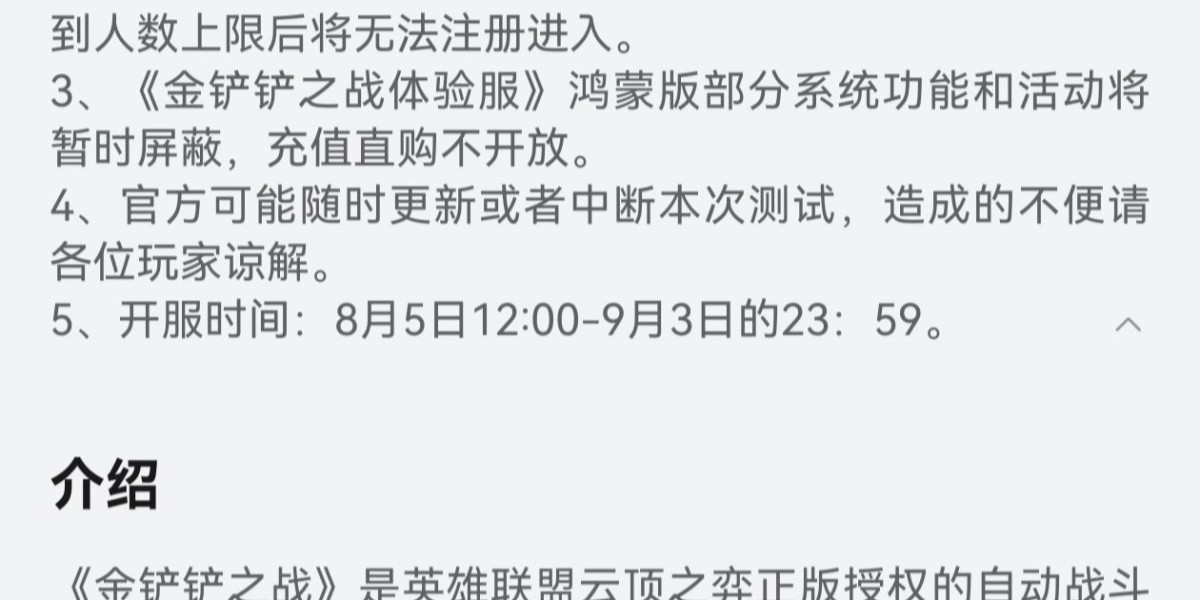本文转自:泉州晚报
小城调酒师
□郑艳艳
(CFP 图)
街市灯火淌成河,一家全黑装修格调的咖啡酒吧却社恐般地挨在一处僻静的街巷口。屋内的灯光那般微弱,衬得吧台后的那个身影好似融于静谧孤独的夜色中。
推门而入,我终于将那个身影看得清晰了。黑色花衬衫,一束长马尾垂在牛仔帽后,乍看带着点离经叛道的锐气。没错,这位年轻的调酒师,确是我的学生小南。听见我唤他,他猛地抬头,眼里炸开惊喜,笑容还是那般纯澈温暖。
我好奇他如何与调酒结了缘,他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第一次看到调酒师晃酒壶的样子,就着了迷,偷偷学了一阵子,便萌生了当调酒师的念头,只是一直不敢跟父母说。”后来他去当兵,梦想暂时封存。退伍后,他一头扎进酒吧当学徒,洗无数的杯子,研究不同款鸡尾酒的配方,练习摇酒累到胳膊抬不起来。他自嘲道,第一次调的酒简直惨不忍睹,他特意拍了照,留着当“成长纪念”。
我点了一杯“似花亦非花”,诗意的酒单,一看就是小南的风格。
“OK!”他打了个响指,转身娴熟地将苹果切成均匀的薄片,用捣棒将剥好的葡萄打成汁。他手持勺子搅动玻璃杯里晶莹剔透的冰块,手法优雅地通过双头量酒器将淡青色、琥珀色、紫色的液体依次注入杯中。“再加点破碎的小青柠,口感更佳。”话音落下,这一杯泛着细碎白汽的液体,便被收进三段式摇酒壶。
“啪!啪!”他扣好摇酒壶的顶盖,双手握住酒壶两端,不断来回地晃动。酒壶在空中呼呼作响,冰块碰撞的脆响混着低低的爵士乐,小南的脸因为专注和使力微微泛红。片刻后,一杯点缀着翠绿迷迭香、紫色绣球菊、橙黄干柠檬片的鸡尾酒惊艳登场。
我问他,摇酒有时间规定吗?他说有的,初学时他用秒表掐着,现在光听冰块撞击声,就知道酒与冰融到了几分。“天天摇,肱二头肌练出来了吧?”对于我的调侃,他咧嘴笑着,有些得意地答:“那是自然。”
他又给我斟了一杯自己酿的杨梅酒,跟我干杯,聊着他当年一些同学的现状,有的结婚生子,有的接管家业,而他,这么多年了,还在与家人僵持。父母盼着他接手家里生意,可他偏想守着这方吧台。果香裹着微醺漫上舌尖时,他眼里闪过一丝怅然:“他们不懂我的快乐,但至少,这份快乐能让我养活自己。”
我暗自叹一口气,我理解他的执着,更理解为人父母的期盼。我也心疼他的作息,晚上七八点到凌晨三四点,长期熬夜身体会扛不住的。他乐呵呵地说,他每天都会起来吃早饭,后面再补个午觉,把生物钟一点点掰平衡。
每一个成年人都非常需要治愈。我想问他调过这么多酒,治愈过多少人,是否也治愈了自己?但我忍住没开口。我们都很清楚,心灵的伤痛绝对不是靠一杯来自某个特定地域的咖啡,或者一杯造型别致、口感奇特的鸡尾酒就能治愈的。
客人纷至沓来,我退到卡座,小南则和着音乐的节奏轻微地摇晃身体,开始调着下一杯“破春”,下一杯“似花亦非花”……
我听着顾客的惊叹,听着他与这群年轻人偶尔夹杂着英文、法文词汇的笑谈,不禁眼眶一热。我明白,哪怕他此刻表现得多么热情多么快乐,他的内心一直都在渴望,渴望被家人“看见”——看见他调的酒里有星光,看见他看似“不务正业”的价值所在、心之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