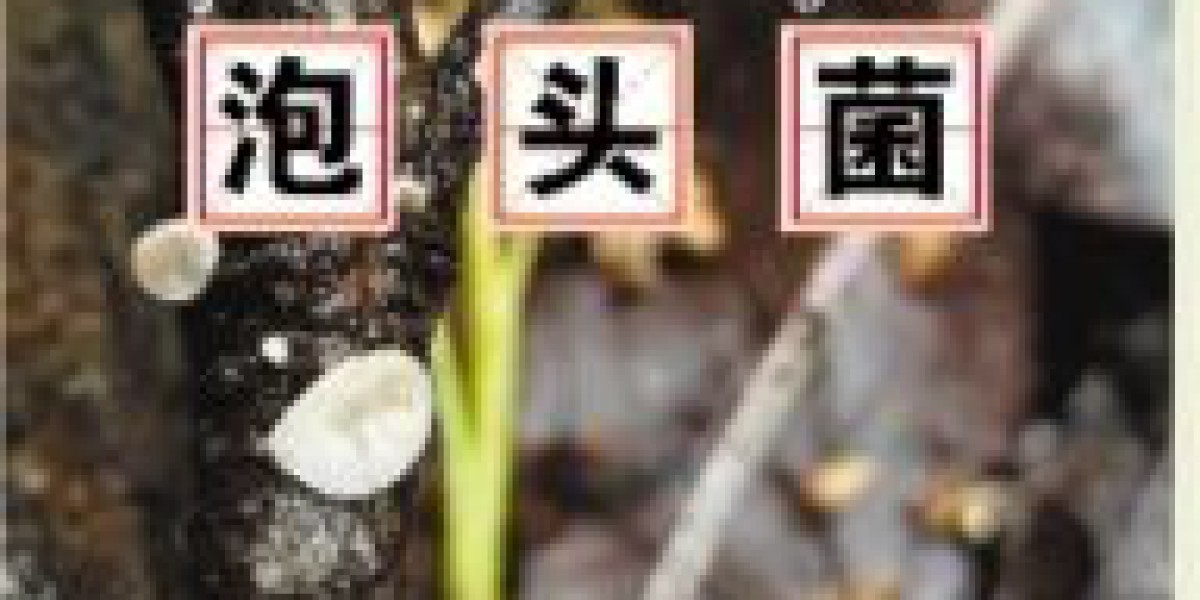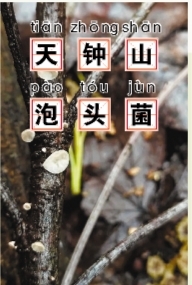本文转自:杭州日报
记者 骆炳浩
我是一枚娇小的真菌,隶属于蘑菇目泡头菌科泡头菌属,隐居在富春江南岸的密林里。
在这座被苏轼、朱熹诗文浸润的山林中,晨雾是我的面纱,阔叶林枯枝是我的禅床。在雨露的滋润下,我悄悄探出软革质的子实体,以杯盏之姿承天露,以素白之身映山光。
苔藓们常笑我痴愚——她们追逐着斑驳的阳光,在树影间编织翠色的锦缎。而我独爱这幽暗处的清明,静静聆听从远处传来的天钟禅寺梵音。偶尔有松鼠踏过我的家园,它爪尖带起的微风,于我已是惊涛骇浪。
2023年的一个清晨,我照常进行着生命的仪式——从菌盖边缘渗出细密的水珠。这些承载着孢子的甘露,本应等待一只偶然经过的飞虫,却不料等来了一双格外温柔的手。
调查队员的指尖轻触我直径不足1厘米的白色身躯,显微镜下我的菌丝脉络第一次映入了人类的眼睛。科研人员比对基因数据库,最终确认我是一个全新的真菌物种。因为首次在天钟山被人类发现,因此得名“天钟山泡头菌”。
我的名字带着山水的印记。“天钟山”三字不仅标注地理坐标,更承载着千年人文。蒋毅复笔下“高峰插云,深涧夹雪,寒瀑奔腾,白石清泉”的意境,正是孕育我的自然圣殿。而“泡头菌”这个物种名,则源自我们家族特有的泡囊状结构——这些微小的胞囊如同自然赐予的珍珠,在显微世界里闪耀着进化智慧的光芒。
2024年3月21日,我的拉丁学名Physalacria tianzhongshanensis载入真菌学国际权威期刊《Mycology》,收录于生态环境部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大型真菌卷》名录,并被评估为DD等级。
但我的故事远不止于学术发现。在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描绘的山水间,我们这些微小真菌正在书写着永不落幕的生命诗篇——用菌丝连接古今,以孢子的语言吟唱生态文明的密码。
守护者说
“人类与大自然最美好的距离,是相望而不相扰,相知而不相犯。”富阳天钟山旅游有限公司负责人袁波说,当媒体报道引发关注时,天钟山景区并没有因此忽略科学守护,他们选择不立指示牌、不标坐标,不将天钟山泡头菌的栖身处变成观光点。袁波说,真正的保护不是划地囚禁,而是给它自在生长的空间。